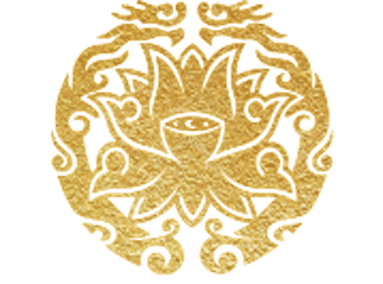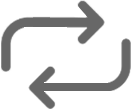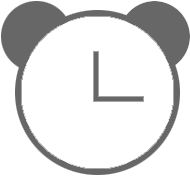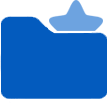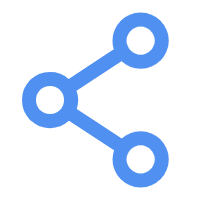【此文稿为初打内容,未经仔细校对,强烈建议结合音频阅读】
今天是五一云共修的最后一天,上午听完课,下午和晚上还要打坐。打坐结束以后,美国的凌晨2点,中国的下午5点,会举行一个禅七的结束仪式——解七,希望大家参加。
禅七虽然结束了,但课没有讲完。内容我起码已经省了一大半,今天能把儒家讲完,但自宗还没开始讲,如此结束的话,好像把“本”掉了,有点不大合理。也就是说,禅七完了,但关于这期的交流内容还没完,那怎么办呢?中国时间的星期六和星期日,中午的10点-12点,接着把佛家的哲学讲完,主要是唯识、中观,还有一些如来藏的哲学,如此一来,就能显出佛家及东西方哲学的差别点在哪里。
众所周知,佛家与东西方哲学的差别在于“般若”,至于般若为什么是佛教最突出、最尊贵的特点,禅七结束以后,会接着来讲。虽然后面的交流不在禅七的活动之内,但没办法,禅七就七天,按照惯例只能就此结束。
儒家禅定
今天继续交流儒家的哲学,昨天讲了一些儒家的观点、见地,现在来讲儒家的禅定。儒家的禅定,并不是后期王阳明心学派才开始的,从孔子时代就有,在典籍上不太突出,但也看得出来一些,最典型的是道家的经典《大宗师》,里面说到了儒家孔子的故事。
道家为了彰显自己的厉害,老是嘲笑孔子,用了孔子跟弟子的问答,说了一些关于禅修的问题,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明,儒家也有禅定的历史。那有没有可能是道家瞎编的呢?现在是讲理义,若要去考证,好麻烦的,也没办法考证。
说老实话,我根本不相信历史,为什么呢?那时发生的具体事件、具体时间,我可能会相信,确实有秦朝、汉朝、唐朝,这没办法否定。同时,能看到很多大事件的发生,比如战争、大灾难等等,也留下来了很多典籍,这些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,我们不能否定。但是历史上记载的东西,很多都是记载人自己的思想、看法,比如《史记》里面的好多东西,现在就能把它推翻。太史公、司马迁都是非常认真、严肃的史学家,绝对不会信口开河,就算是这样,都没办法做到绝对的真实。
原因是什么呢?每个人看一个事情都有角度、有局限,里面对君王等历史人物的评价,你怎么知道是准确的呢?比如,历史书上把隋炀帝评价得如此不堪,但据考证,原来他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,而且说法不一。还有李世民,千古一帝唯一的污点就是杀了自己的两兄弟,但据史料记载,在他统治的过程中,也有很多麻烦的地方。
所以,真实的历史我们是没办法真正的清楚,只能知道大概。那么,做过的历史,谁能完全清楚呢?完全清楚的只有佛陀或者大菩萨,甚至我们都不清楚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对自己的影响。比如抑郁症患者,或者弗洛伊德说的在潜意识中受过伤的人,原因是他们不清楚自己。比如小时候受过很重的伤,长大后的生活、情绪、思考,都受着过往经历的影响,但自己却不清楚。连自己都不清楚,还要想清楚那么长的历史,或者靠一些文字、说法、纪录片,就想全面的、清晰的知道历史,显然不可能的,所以我说不相信历史。虽然我说不相信历史,但也不是完全的不相信,比如我不相信发生过秦朝、我不相信发生过汉朝、我不相信有四书五经、我不相信有孔子……那就是在扯淡,这些大体的东西我是相信的,但历史的细节我们真的不清楚。
言回正题,现在来讲孔子的弟子颜回打坐的故事,这个故事不是儒家经典中记载的,而是一部嘲讽儒家的道家经典,从侧面反应了,儒家很早以前就有禅定了。
1)孔子
颜回曰:“回益矣。”仲尼曰:“何谓也?”曰:“回忘仁义矣。”曰:“可矣,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,曰:“回益矣。”曰:“何谓也?”曰:“回忘礼乐矣!”曰:“可矣,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,曰:“回益矣!”曰:“何谓也?”曰: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蹴然曰:“何谓坐忘?”颜回曰: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,此谓坐忘。”仲尼曰:“同则无好也,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!丘也请从而后也。”《大宗师》。
孔子有三千弟子,七十二贤人,其中其中最厉害的、最受推崇的是颜回。有很多夸张颜回的故事,比如遇到艰难困苦,面不改色,勇往直前。有一次,颜回去找孔子汇报自己修行的成就,自称得到利益了、修行有感觉了——“我突然发现心原来在左边,因为我从右边看过去……比如我的心从身体里面跑到外面了……我有一个境界,眼前一片白茫茫……”
孔子(“仲尼”是孔子的字)问他得到什么利益了?颜回说我已经忘了什么是仁义了。孔子的学生都要求仁义礼智信,还要克己复礼,坚持仁术,那为什么作为弟子的颜回会忘仁义呢?这里的“忘”并不是遗忘的忘,而是说仁义完全融化在相续里面,连思考都不用了。就像单空修行到很厉害的时候,会直接觉得就是单空,不会想“用光去射、它根本没有实质”等概念。这时候完全成了一种境界,自然而然,仁义本来如此,故忘仁义矣,意思是不喊口号了。如果反复说一个事情,就说明他对这个事情不见得理解,就像关系很好的两个人,不会天天出去吹嘘“我跟你很好哦”,有时候反而表现出一些不好的行为。同理,仁义熏习透了以后就忘了,所以叫“回忘仁义矣”。
孔子说确实不错,但没达到很高的境界,差的距离还很远。隔了一段时间,颜回又来拜见孔子,说我又得到以利益了,即境界又提升了。孔子问是什么利益呢?颜回说:“回忘礼乐矣!”孔子讲究克己复礼,不仅仅指人与人相互的礼貌,礼是一种次序,在你的位置就做你该做的事、遵守你该遵守的行为规范。在古代,大臣就有大臣的规矩,大臣所穿的衣服、用的车马都有讲究的,这就叫礼,不能僭越,否则要杀头的,必须遵守周公那时候建立的礼。大家不要把“礼”想成礼貌,见面很客气等等,其实不然,包含的范围其实很广。
孔子非常重视礼乐,乐也是一种礼制,在某个环境里面的什么人,就用什么样的音乐都是有规定的。比如连续剧《雍正王朝》,雍正做太子时征战回来,对方为了刁难他,故意用君王打胜战回来演奏的音乐迎接他,雍正马上警醒起来,如果接受的话,对方会去康熙皇帝处告他僭越,因为这时候不该用这个音乐,不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,表明有夺权的野心。
儒家也讲究听音抚琴,,比如“孔子闻韶音,三月不知肉味”,孔子听到韶山那块地方的音乐(不是指韶山,是指那块地方的音乐。当然,“韶”也有人解释为清雅的意思),三个月都沉浸其中,连吃肉都没有味道了——真是音乐狂啊!从而可见,孔子对礼乐非常重视,但作为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说:“我已经忘掉礼乐了!”意思是什么呢?关于礼乐的规矩、次序性的东西,对音乐的深入理解,已经完全了然一心,不必要整天提醒自己,这就叫“回忘礼乐矣!”孔子回答说:“还是有距离。”
下次又见面,颜回又说得到利益了,孔子问是什么利益呢?颜回说:“在座中,我已经做到忘了一切,叫坐忘。”“忘”没有说具体的内容,没有说音乐,也没有说礼制,也没有说仁义等概念性、道德性的东西,就一个“坐忘”。孔子突然很正经的说:“何谓坐忘?”
下面颜回的回答很精彩,儒家禅定的准则就在这里了,或者是说儒家禅定的境界性禅定就是这样的。“堕肢体”,肢体的觉受没有了,就像打坐的时候身体没有了——这个很难的,我们打坐的时候很难忘掉身体,一会儿屁股疼,一会儿腰酸,一会儿双盘压得左边没感觉了、左边的脚不属于我的了、右边的脚也差点不属于我的了,这都是没办法忘掉自己、没办法堕肢体。“黜聪明”,聪明就是各种念头、想法、情绪也没有了,或者一会儿去关注某种感觉、某种觉受都没有了。“离形去知”,连去认知外境的心,或者著在有形有相的事物上的东西都没有了。“同于大通”,汇入通达的境界里面。至于大通是什么,这里没有详细的解释,如果用佛家去解释,就是汇入般若、汇入究竟觉知,如果用道家去解释,就是进入恍兮惚兮、其中有精、其中有象,这里只是用了“大通”这个词汇。“此谓坐忘”,这就是坐忘。
按照我们这帮经常闻思修的佛教徒的说法,就是单空修到身体的触识消失、眼识也消失,进入一种似乎明了一切的状态。这有几种可能性,一种是阿赖耶识的状态,一种是阿赖耶识生起的神通境界里面,一种是真的证悟、明白了法性。所以,“同于大通”是个很模糊的词,中国的文字很麻烦,描述修行的东西很模糊,汉语就有这样的特点,一字多义。你说:“是吗?”是的,确实如此。但再确切地问:“是吗?”里面可能有很多状况,不一定是的。
孔子又作了一些解释,“同则无好也”,“同”指没有好坏的区分,无好无坏、不来不去;“化则无常也”,这种状态完全消失了各种各样的执着、生灭,“无常”就是生灭的意思,“化则”有点像空性的意思。准确来说,应该是“化则无无常”,不能就是无常,或者就是常,因为化了无常。如果同,就汇在一起了,没什么好坏比较,也没有生灭,就化了无常。
按照佛家的理解,应该是“化则无无常也”,这样一来,可以理解成常见。“化则无常”可以读成化于无常,就是融在事物之中,常与无常之间、无常与常中,没有好坏生灭的意思。“而果其贤乎”,这样的结果太好了。“丘也请从而后也”,我也跟随着你来学习。
“化则无常也”,也可以理解成融化在普通的事物中,化于无常的意思。按照佛教的说法,“同则无好也,化则无无常也”,反而是“化于无常”好,因为无常的极点就是空性,这样去理解也可以理解到最顶端去,但到底是不是呢?儒家里面是找不到像佛家那样很具体的中观、唯识学说、把般若描述得如此清楚,从理论到实践到果实,只有佛教才有,他们只有似是而非的语句而已,所以很麻烦。不管怎么样,证明儒家有禅定,而且越到后期就越重视,禅定也越来越细,到了陆王心学,打坐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有人问:“为什么要从陆王心学开始才有打坐呢?”说到儒家,一定会提到陆王心学,有师兄跟我说:先秦时期或者秦汉时期的儒家,跟后期陆王心学的儒家不一样,开始的时候没有道、佛的融合,基本上都是一些社会伦理,不像陆王心学那样牵涉到世界的本质与对心性的了解,所以前期不应该叫儒家——不能这样说,王阳明和陆九渊虽然都有自己的理论,但还是得承认是孔丘的后人。
儒家的理义是变化的,而佛教的理义是没有变化的,因为佛家的理论没有发展,只是根据不同的人、不同时期的相应展示,理论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一解释,就到了顶点。但是,儒家必须得承认有发展的,后期的发展不能说自己不属于前期的分类,人家自己都承认,你却硬要把它分开,真没有必要。你要这样分开来认识,也没有关系,也有师兄这么来问,在此就顺便说一说。
2)孟子
公孙丑问曰:“敢问夫子恶乎长?”曰:“我知言,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?”曰: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;无是,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,则馁矣。
公孙丑问孟子:“夫子您最擅长、最牛的是什么东西?”孟子说:我知道,我善养浩然之气。”什么是浩然之气呢?孟子说:“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。表象为气,但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。”儒家经常说“养气”,什么叫“直养”呢?放弃不好的心,把儒家所说的仁义道德的正气养起来,或者直接去培养这个气。人的念头是受气影响的,如果心思过分扭曲和分散,那就不叫直养,气用多了就会气馁,或者气很阴、气无力。“直养”就是少些念头,多些正能量的念头,也叫正气,不要以线曲的、分别的、复杂的情绪去培养气。
儒家总是说天人合一,孟子也赞同,这个“气”不仅仅指体内的气,还可以使天地之间都充满正气。关于气的学说,中国文化厉害得很,认为整个宇宙的基本物质就是气。《红楼梦》里面说:天下有个至大至纲的气,就成了天;至阴的气,就成了地;很灵的气,伏在人的身上,这些人愿当帝王、将军、臣相等大人物,也绝对不愿意做凡夫走卒等庸人。
中国文化对“气”的描述有很多,孟子说他养的是浩然之气,这种“气”不单单是内心的一股正气,还可以“则塞于天地之间”,由人即天地,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。
“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”,充满了这种正气,就能坚持仁义道德。“无是,馁也”,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气馁。气馁就是气变得弱小,不能至大至纲,小理小气的,指这个人充满了邪气。很多时候,“气”指一个人的精神面貌,比如说这个人好阴气啊!“气馁也”,就是气弱了,如果不去养气,就会显得很弱。“直养”,就要平复念头和情绪,即打坐。所以,千万不要认为养气是好大的事,其实就是打坐、禅修。
“是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也”,集仁义道德,才能产生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,是自然产生的,非利益强行去抓取的,是去功利的。“集义”指堆集正气、正义的东西,慢慢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。其中有行为的成分,要配合仁义道德,处处都是正能量(大家要正确理解“正能量”这个词汇)。“非义袭而取之也”,并不是功利性或道理的指向,“袭”就是拿取、指向的意思。
“行有不慊于心,则馁矣”,行为会让你的心产生厌恶,非直养、没有坦荡的浩然之气,叫做“不慊于心”,这样的话,“则馁矣”,气又会变得弱小。这里说明什么意思呢?行和坐都必须养浩然之气,可见儒家是怎样培养自己的身心。
3)二程(二程指程颢、程颐)
谢显道(即谢良佐)习举业已知名,往扶沟见明道先生,受学志甚笃。明道一日谓之曰:“尔辈在此相从,只是学某言语,故其学心口不相应。盍若行之。”请问焉,曰:“且静坐。”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。([宋]朱熹编《二程外书》卷十二)。
伊川指面前水盆语曰:“淸静中,一物不可着。才着,物便揺动。”([宋]朱熹编《二程外书》卷十二)
谢显道也是一位很出名的大儒,他考上了举人。“往扶沟见明道先生”,去扶沟(地名)见明道(程颢的字明道);“受学志甚笃”,准备跟随程颢学习,“甚笃”指求学的心非常坚定。
明道一日谓之曰:“尔辈在此相从,只是学某言语,故其学心口不相应。盍若行之。”有一天,明道跟他说:“你们跟随我学习,但只学我的语言,学不到我内在的东西,心口不相应。”“盍若行之”,那要怎么办呢?“盍若”就是如何的意思。众人问怎么办呢?程颢说:“且静坐。”“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”,程颐的字伊川,说明儒家到了二程就非常重视静坐。
程颐指着面前的水盆说:“打坐的时候,心不能附着在任何一个东西上,像面前的水一样,如果耽著在一个事物上,水就开始动了。”
禅定有几个阶段,可以用五种状态来比喻。第一种状态,就像瀑布的流水一样无法控制;第二种状态,就像急流穿越峡谷一般,有时专注得很好,有时却像急流撞到岩石,形成漩涡,然后回归宁静;第三种状态,就像河流中的水潭,干扰会产生涟漪,其他时候则平静无波境;第四种状态,就像波浪的海洋,生起种种的心灵构想,就算再巨大,只要略提正念就立刻平息下来;第五种状态,就像无波浪的海洋,无论发生什么事,海洋都维持不动。同样,儒家也有打坐的经验和感受。
4)朱熹
我一直以为只有个别人不喜欢朱熹,后来我发现,不喜欢朱熹的基本上都是女的,原因是什么呢?因为朱熹的理学对妇女不公平,但是太公平也挺麻烦。在此,我不想过于评价,否则会觉得我像朱熹一样对女性不公平。其实释迦牟尼佛也对女性不公平,比丘的具足戒只有两百五十条,比丘尼则有三百四十八条,在经书上说:女人是五漏之身,一不能成梵王,二不能成帝释,三不能成魔王,四不能成转圣王,五不能成佛道。佛在《大爱道比丘尼经》中慈悲宣说“女人八十四病态”,林林种种,是不是对妇女不公平?其实不然,应病与药,针对女性的毛病给与相应的药。
佛家的基础思想,认为所有众生都是佛,如果偏向这个、偏向那个,就不是菩提心了。缘一切众生,视所有众生为母,可见多爱女性啊!为什么不说“视所有众生为父”呢?从男性的角度,会觉得“视所有众生为母”不公平,有38妇女节,还要搞一个39丈夫节——其实不然,因为你有这样的状况、毛病,就给你相应的方法,起码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。
那儒家是不是这样呢?我想,大儒们至少不会那么彻底的蔑视、践踏女性,只是后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,还有一些风俗习惯,导致对妇女们不公平,特别是发展到生理上的缠小脚,超级变态。
(静坐)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,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九)
静坐能让心安静下来,才可以穷理,把道理想清楚。“存心静虑”是儒家的词汇,意思是把心放在那里,不要动它,也就是静虑。“穷理以虚心静虑”,“虚心”指心不能著在一个地方,不能自以为是、强行地认定一个观点,不仅仅是谦虚的意思;“静虑”指静静的思考。
佛家说的禅修,很大部分指静虑,并不一定指禅定。请记住,静虑和禅定是有差别的,禅定指彻底的修定,让心静下来。不仅仅佛教是这样,任何外道都是这样,现在说的儒家,对于佛家来说就是外道。静虑是有思维的,要体会很多东西;禅定是什么都不思维、不体会,把意识停下来而已。
静坐非如坐禅入定,断绝思虑,只收敛此心,使毋走于烦思虑而已。此心湛然无事,自然专心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)
这是一些关于禅修、静坐的说法。这时候,佛家的禅修已经进来了,但他们不会认为禅宗很厉害,儒、道、佛三家在历史上,有时候互相勾搭,有时候互相排斥,又融合又排斥。
“静坐非如坐禅入定,断绝思虑,只收敛此心”,我们静坐并不像佛家的禅宗,坐禅入定断绝思虑,由此可见,禅定跟禅思真的不一样;“使毋走于烦思虑而已”,不能坐在垫子上东想西想,思虑绵绵,不受控制。“此心湛然无事,自然专心”,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而不耽著在任何事上,就专心了。
这是朱熹对静坐的看法,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,但你做得到吗?普通人一上坐,念头犹如不受控的急雨,一会儿这、一会儿那,大部分人刚开始静坐一定是这样的。而收敛此心,使毋走于烦思虑而已,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,刚开始要先修禅定,让心静下来,慢慢才能做到。怎么能让心湛然无事呢?很难的!当然,也有人坐在那里养浩然正气,心无邪、无邪思、无邪想,慢慢地,也会变得湛然无事,这是儒家对禅修的看法。
郭得元告行,先生曰:“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,闲人客省见得一两人也,济事若浑身都在闹场中,如何读得书?人若逐日无事,有见成饭吃,用半日静坐,半日读书。如此一二年,何患不进。”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一十六)
郭得元是朱熹的弟子,有一天他来辞行,朱熹就说:“如果少见两个人、少说两句话,用半天读书、半天静坐,坚持两年,功夫学问就会有所长进。”这里说的是“半日静坐、半日读书”,直接就说静坐了。
无事静坐,有事应酬,随时处无非自己身心运用。但常自提撕,不与俱往,便是工夫。事物之来,岂以漠然不应为是耶?((《荅林徳久》,[清康熙]《御纂朱子全书》卷一)
这段话也很精彩,没事的时候就静坐,有事就去应酬,有点像禅宗描述证悟本性以后的词句——“胡来胡现,汉来汉现”。“汉”指汉人、汉族的意思,“胡”指外族、外人的意思。意思是什么来了就现什么,但心不跟随——“事来有应,事过无痕”,事来了去应对,事过了完全不去牵挂,坦坦荡荡,无牵无挂。
“随时处无非自己身心运用”,不管什么时候、不管多大的事,无非都是身心在运用。“但常自提撕”,就是我们常说的提起觉知,常常把静坐的方法运用出来。“不与俱往,便是工夫”,不要跟着事情跑,不要整天焦虑忧愁,过去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,现在心静坐,便是工夫。“事物之来,岂以漠然不应为是耶”,事情来了,并不是不理才是正确的,而是理完以后就算了。
这话是朱熹说的,听起来很对,实际上是有毛病的,为什么呢?第一,你能做得到吗?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你,面对不关心的事,当然可以事过了无痕,但面对太关心的事,就另当别论了,比如你欠我五块钱、甚至五千块钱都没关系,但欠了五十万,那就另当别论了,我会天天想着你什么时候还我,所以,要看什么样的事。第二,你做到哪种程度?能不能了生死?平常事都可以,遇到大病、大灾难还能这样不受影响吗?而朱熹没有提到这些东西,如果不证得般若,不像佛家那样走到究竟,就很容易流于表面。
5)王阳明
王阳明的禅修很厉害,在中国汉文化里面,儒家后期最受推崇的两个人,一个是王阳明,一个是曾国藩,都是儒家三不朽(立功,立德,立言)的代表人物。而且两个人都有军功,在朝廷的军队没来之前,王阳明就把造反的宁王收拾了;当时少数民族起义,很难镇压,最后王阳明过去搞定了。这就是他的军功,而且他的道德很高尚,是心学的极大成者,书籍《传习录》流传于世。曾国藩也有军功,镇压太平天国起义(有人说他杀人太过,被人称为“曾剃头”,到底杀人过不过,很难用我们的是非观念去判断);立德方面,曾国藩也道德高尚,是忠君的典范;立言方面,所著的书籍连林彪都天天拿着来读。
这两个人在儒家里面很受推崇,王阳明就更厉害了,影响到日本两大军神,其中一个是东乡平八郎,他是海军的军神,一生中,身上都挂着一个腰牌,上面刻着“一生俯首拜阳明”。老蒋也很佩服王阳明,后来他到了台湾,在一座很漂亮的山里修了自己的官邸别墅,把那座山取名叫“阳明山”。王阳明的影响很大,打坐的功夫也很厉害,他有很多关于静坐的故事。在一次领军的路上,他在帐篷里面打坐,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龙吟声(特别是道家的修禅,养气到一定时候,有时会发出这种声音),声传数十里,一众军民皆惊。下面来看,王阳明是怎么打坐的呢?
一日,论为学工夫。先生曰:‘教人为学,不可执一偏,初学时心猿意马,拴缚不定,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,姑教之静坐、息思虑。久之,俟其心意稍定,只悬空守静如槁木死灰,亦无用,须教他省察克治。省察克治之功,则无时而可间。如去盗贼,湏有个扫除廓清之意。无事时,将好色、好货、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,定要㧞去病根,永不复起,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䑕,一眼㸔着,一耳听着,纔有一念萌动,即与克去。斩钉截鐡,不可姑容,与他方便,不可窝藏,不可放他出路,方是真实用功,方能扫除廓清,到得无私可克,自有端拱时。(《传习录上》,《王文成全书》卷一)
先生说,“教人为学,不可执一偏”,教人学习心学,不可让人偏到一方,偏哪一方呢?怎么偏法呢?要么老是让人学习很多知识,要么老是让人打坐,都叫执偏。“初学时心猿意马,拴缚不定,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,姑教之静坐、息思虑。”初学的时候,人有很多思虑,你要教他静坐。“久之,俟其心意稍定,只悬空守静如槁木死灰,亦无用,须教他省察克治。”如果你长期这个样子,变成一个死禅定也没用,需要观察自己内心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怎么观察呢?“省察克治之功,则无时而可间。如去盗贼,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。无事时,将好色、好货、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,定要拔去病根,永不复起,方始为快。”这很像佛教的忏悔,对治贪嗔痴慢疑。那要怎么办呢?“常如猫之捕鼠,一眼看着,一耳听着。才有一念萌动,即与克去。”一有念头即以扫除,而且不一定在打坐中,平常都要这样,一起念头就要反观,又有打坐又有反观,内格格物就是如此。
“到得无私可克,自有端拱时在”,到了内心完全坦坦荡荡,没有各种私欲念头的时候就是端拱(什么叫端拱呢?端庄,儒家里做拱礼,代表非常恭敬的意思,那时候会“拱手相敬”,指到达了一定的境界),这是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中记载的。(《传习录》现在出版的一共有四本,大家可以去找来看,上面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。如果你是学佛的人,完全不用这样去看,古文读起来七拱八翘的,还不如把佛家的中观、唯识、禅修搞会,再回过头去看,随随便便,怎么都能看懂。)
九川问:“近年因厌泛滥之学,每要静坐,求屏息念虑。非惟不能,愈觉扰扰,如何?”先生曰:“念如何可息?只是要正。”曰:“当自有无念时否?”先生曰:“实无无念时。”曰:“如此却如何言静?”曰:“静未尝不动,动未尝不静、戒慎恐惧即是念,何分动静?”曰:“周子何以言定之于中正仁义而主静?”曰:“无欲故静,是‘静亦定,动亦定’的‘定’字,主其体也。戒慎之念是活泼泼地。此是天地不息处,所谓‘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’,一息便是死。非本体之念,即是私念。”又问:“用功收心时,有色在前,如常闻见,恐不是专一。”曰:“如何不闻见?除是槁木死灰,耳聋目盲则可。只是离闻见而不流去,便是。”曰:“昔有人静坐,其子隔壁读书,不知其勤惰,程子称其甚敬。如何?”曰:“伊川恐是讥他。” (《传习录下》,《王文成全书》卷三)
九川是王阳明的弟子,“近年因厌泛滥之学,每要静坐,求屏息念虑,非惟不能, 愈觉扰扰,如何?” 近年因为学得太多了,想要静坐,然后“求屏息念虑”,“屏息”不是指不呼吸,而是细微的意思,不完全把它卡住,“屏息念虑”是让思维和气息细微下来(打坐时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细微,若想检验定的程度,就用一根很轻的鹅毛放在鼻孔前,鹅毛不动就说明此人在很深的定中。因为他的气息非常的细微,念头跟气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,这里的“屏息”并不是指完全不呼吸,那岂不是卡死了,而是指呼吸非常细微。)
“非惟不能, 愈觉扰扰”,本来想让念头平息下来,反而很烦恼,很多人打坐也会如此,那怎么办呢?先生曰:“念如何可息,只是要正。”你不必去要求念头,只是念头起来不要堕于贪、私。儒家最讲公正,不能私,私就是贪嗔痴等很不好的念头。这里说有正念就可以了,其实佛家有时候也这么说,八正道首先就说要有正念、要保持正念。关于什么是正念,儒、佛、道各自的正念是不同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正念是每个派别的究竟见解引出来的,合乎佛教的究竟见解就叫正念,不合乎的就不叫正念。所以儒和佛的“正道”也是不一样的。
曰:“当自有无念时否?”这样下去,会不会走到完全没有念头的境界?先生曰:“实无无念时。”说明王阳明的禅定不咋地,当然,也可以说很深,因为最高的禅定(非想非非想定)都有极其细微的念头,按照这种说法,王阳明的“实无无念时”是成立的。如果不那么学术性地去看,确实可以体会到四空定的层面(空无边处定、识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想非非想处定),哪怕到四禅中的舍念清净,都已经体会不到念头了,而王阳明却说“实无无念时”,也可以说他连四禅都没到。
关于“实无无念时”,要看从哪个级别去看。如果是粗大的念头,到四禅都没有;如果是非常微细的念头,到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时候还会有。也就是说,你看一个事物是用什么倍数的显微镜去看的,如果显微镜的倍数很高,还可以看到更细微的东西,如果显微镜的倍数不咋地,就会觉得什么都看不到,所以,“实无无念时”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。
曰:“如此却如何言静?”九川就问:这样的话,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叫做静呢?曰:“静未尝不动,动未尝不静、戒慎恐惧即是念,何分动静?”静并不是不动,动也未尝不静,儒家里面讲究“戒慎恐惧”,“戒”就是不能做什么东西,比如儒家常说的戒忍、戒急(生气、着急),“恐惧”就是恐惧自己起不好的念头。即使内省自心,也是念头,这时也可以叫做静。意思是说,只要念头正就行了、戒慎恐惧就行了——这里的“恐惧”,不要误会是见到贞子的那种恐惧,而是内省自心时,起了不好的念头就自恐,是一种防范自己生不好念头的方法。所以,这时候也是念头,也可以叫静,而不是那种死禅定,王阳明特别坚持这个。
曰:“周子何以言定之于中正仁义而主静?”周公为什么说处于中正仁义中属于静?曰:“无欲故静,是‘静亦定,动亦定’的‘定’字,主其体也。王阳明回答没有欲望就是静。如果你处于中正仁义中间,有念头和无念头都是定。“主其体也”,处于中正仁义或者正念充满的时候,不管你的心有念头还是无念头,它都是“定”。这个“定”是说我们心的本体处于正气、正念中间,而并不是说一个安静的东西。由此可见,儒家跟佛家真的不一样。
“戒慎之念是活泼泼地”,戒慎之念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,不是死的状态。“此是天地不息处”,这正是天地不停地生化、不停地运转的原因。“所谓‘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’,一息便是死。非本体之念,即是私念。”所谓维系天的运转,并不是一个非常死的东西,只要不是本体正确的念头,那就是私念(有欲望的念头),就不是维持天地正常运行的正确念头(说白了,就是要充满正气)。心处于中正仁义就是静,而不是一种安静的禅定,这是儒家对定的认知。“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”,周正、庄严的念头一直运行下去。“一息便是死”,一停下来就是死,所以天地一定有念头,这个很像阿赖耶识。“非本体之念,即是私念”,如果不是这样的念头,它就是私念。
又问:“用功收心时,有色在前,如常闻见,恐不是专一。”用功收心的时候(修静的时候),有景象现前,如果像平常一样去看见它、听见它,这就不是专一了、就不是在收心修静了。曰:“如何不闻见?除是槁木死灰,耳聋目盲则可。”王阳明反问他: “什么是不看到它、听到它?除非你的心完全像槁木死灰一样,耳朵聋了,眼睛也看不到了。“只是离闻见而不流去,便是”,你可以看到它、听到它,但是不要跟着他跑,照见万物而不随万物而动。其实不然,只要照见万物皆空,随便它流去也行。如果照见万物而不流去,也就维持一个平静的心而已,他把平静的心理解成正念,叫中正仁义,没有私念头。
曰:“昔有人静坐,其子隔壁读书,不知其勤惰,程子称其甚敬。如何?”曰:“伊川恐是讥他。”有人告诉王阳明,他的儿子在旁边读书,而他在打坐,所以不知道儿子的读书是勤快还是懒惰,程子(二程)就说这个人静坐慎敬(儒的二程特别讲究持敬,内省、内察即静坐的意思)。意思是什么呢?其实是告诉王阳明,有人静坐的时候,儿子在旁边读书,也不知道他是否勤惰,这种状况连程子(很出名的儒家大德)都称赞其很慎敬(持内敬非常的好),你看如何?事实上在怼王阳明,王阳明就反怼回去:“伊川(程颐的字叫伊川)恐是讥他。”这时王阳明斗机锋,说伊川称赞的慎敬,实际上在讽刺他。
王阳明要求苛察内心,在“四句教”里面有所体现——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意思是什么呢?要审察内心、知善,并不是说一味死定。这跟佛家说的禅定其实有类似的地方,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,关键是正念、察知要走到哪里去。佛教要察知是不是处于般若中间?是不是分别念?分别的本质是什么?带着这样的见地去察知的。儒家要察知中正仁义,二者是不一样的。外在的方法看起来一样,实际上本质不一样,一个能证得般若,一个人能养出浩然之气,成为处事做人的典范,这样才能够去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佛教做的行为不一定会齐家治国平天下,会东家做牛、西家做马,这是一位大禅师说的。
又问“静坐用功,颇觉此心收敛,遇事又断了。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,事过又寻旧,功还觉有。内外打不作一片”。先生曰:“此格物之说未透心,何尝有内外。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,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。这听讲说时专敬,即是那静坐时心,功夫一贯,何须更起念头。人须在事上磨炼,做功夫乃有益。若只好静,遇事便乱,终无长进。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,而实放溺也。”后在洪都,复与于中国,尝论内外之说。渠皆云物自有内外,但要内外并着功夫,不可有间耳。以质先生,曰:“功夫不离本体,本体原无内外,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,失其本体了。如今正要讲明功夫,不要有内外,乃是本体功夫。”是日俱有省。(《传习录下》,《王文成全书》卷三)
又问“静坐用功,颇觉此心收敛,遇事又断了”。九川又问:“静坐用功,觉得心开始收敛了,但是遇到事情又不行了。“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,事过又寻旧”,起个念头,去事上省察,事情过了以后还是一样的;“功还觉有,内外打不作一片”,收敛的功还有,但内外却不能打成一片。
先生曰:“此格物之说未透心,何尝有内外。王阳明说:“格物还没有格透。”格物要内省外察,做到完全的正知、正念,又何尝有内外?“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,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。”比如我们正在说话,你在说、我在听,这时候哪里只是心在内观照呢?“这听讲说时专敬,即是那静坐时心,功夫一贯”,说的时候很专注,持敬心,跟静坐时的心是一样的,也就是说,做事、静坐的时候要保持同一的中正平静、和平的心;“何须更起念头”,这时不需要起其它的念头,宁静平静,事来应事,事去无痕。说起来容易,实际上不那么容易的。
“人须在事上磨炼,做功夫乃有益。若只好静,遇事便乱,终无长进。”如果只是打坐,下坐遇到事情就会乱。这个说法对不对呢?对的。包括很多的学佛人也一样,比如禅修中心的很多人天天打坐,打坐的时候一脸庄严相,身心安宁,一座十几个小时都可以,但下了坐,稍稍一撩就不行了。所以,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,但差别还是在见地。
儒家也这样去磨炼,那磨炼为了干嘛?并不是像佛教一样去明白般若,只是让自己的心不为外境所扰动,然后去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所以,二者的目的不一样,动机也是不同的。心的本体到底是怎么样的,其实王阳明也没有走到极点,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这些。
“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,而实放溺也。”看起来静坐的功夫很收敛、很安静、能坐很长时间,实际上是一种放溺,不咋地,反而是一种误区。禅宗也这么认为,参禅的时候,不是让你去修静坐功夫,只准参一个小时,如果时间长了,一定会逼你下座。以前我去云门寺打禅七,有的出家人不愿下座,直接被抬下来扔出去。他要你坐到上面去参“念佛是谁”,参话头、参公案,而不是让你静下去不起来,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,只是儒家省察是为了什么?他要养浩然之气、养中正心态,佛家是要明白般若。所以,二者真是不一样的,但是用的一些方法大体差不多。
后在洪都,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。渠皆云物自有内外,但要内外并着功夫,不可有间耳。以质先生,曰:“功夫不离本体,本体原无内外,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,失其本体了。如今正要讲明功夫,不要有内外,乃是本体功夫。”是日俱有省。什么意思呢?
后来,在洪都这个地方,又回到中国讨论内外的问题。九川说“物自有内外”,所有事物有内有外、有左有右,纷纭不同;“但要内外并着功夫,不可有间耳”,心的本体要照见内心,也要照见外面,不可有区别。“以质先生”,去问先生(王阳明);先生回答:“功夫不离本体,本体原无内外,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,失其本体了。”功夫是离不开心的本体,心是没有内外,只是后来做功夫的时候分了内外。当我们的心分了内外,这时就失了本体。“如今正要讲明功夫,不要有内外,乃是本体功夫。”如今正要讲明功夫,就不要有内外,这个乃是本体功夫”“是日俱有省”,这天九川有所醒悟明白。
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。先生曰:“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,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。汝若不厌外物,复于静处涵养却好。”(《传习录下》,《王文成全书》卷三)
刘君亮也是王阳明的弟子。当时刘君亮身体有病,想去山里面静坐,王阳明就告诉刘君亮:如果你是讨厌外物想去求静,这样反而会养成骄惰之气。就像现在的很多人,打坐是为了避开很烦的外境,其实这真不是修行来的,佛家也不认为这是修行,有时候跟山中度假差不了太大。而且会导致好静而厌事(不是厌世间的世,是厌事情),什么都不愿意做,只喜欢打坐,是一个骄惰之气。
“汝若不厌外物,复于静处涵养却好。”如果不是因为厌弃外物而去打坐,那就是修涵养的好事了。整个儒家都非常重视心怎么去对外物,因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,要训练自己的心去立功、立德、立言,如果只是陷入静坐,他会很讨厌你的,这就是儒家的禅定。
6)陈献章
陈献章是明代大儒,字公甫,别号石斋,广东广州府新会县(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)白沙里人,故又称白沙先生,世称为陈白沙。(想了解他,可以在网上搜“陈白沙”,他也是一个对静坐有很多说法的人。)
为学须从静中坐,养出个端倪来,方有商量处。《陈白沙集》巻二)
学儒家必须要去静坐。
于是舎彼之繁,求吾之约,惟在静坐。久之,然后见吾此心之体,隐然呈露,常若有物。日用间种种应酬,随吾所欲,如马之御衔勒也。体认物理,稽诸圣训,各有头绪来厯,如水之有源委也。于是涣然自信,曰“作圣之功,其在兹乎!”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,盖以吾所经厯、粗有实效者告之,非务为髙虚以误人也。(《陈白沙集》巻二)
“于是舍彼之繁,求吾之约,惟在静坐。”你要舍去那些纷乱繁忙,若想求得我的窍诀性东西,惟有依靠静坐。“久之,然后见吾此心之体,隐然呈露,常若有物。”静坐久了,你会见到心的本来,虽然看不见,但好像能够露出来。这种说法跟道家也差不了,未见般若,总觉得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东西。
云门禅师说开悟的误区:眼前隐隐有物,这是不行的。首先觉得离不开事相,当离开了事相,就觉得本性好像隐隐约约有个东西,跟儒家说的差不多,这就是没有见本性之前的误区。所以,儒家是求静坐,但真没走到般若那里去,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。
“日用间种种应酬,随吾所欲,如马之御衔勒也。”我们天天做事,随心所欲的时候,要像马套住辔头(辔头就是圣训之理或者体认中正仁义之心境、戒慎恐惧的圣训之理)一样紧套不放。“体认物理,稽诸圣训”,体会各种各样的道理,遵循各种各样的圣人所说;“各有头绪来历”,什么东西都是有条有理的;“如水之有源委也”,就像水流一定有源头一样。明白所有的事出于心、出于慎、出于物理,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不混乱,无非就是做人的清晰明白而已。
“于是涣然自信”,这时候很放松很自信;曰“作圣之功,其在兹乎!”学圣人的功夫就是这样的!“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,盖以吾所经厯、粗有实效者告之,非务为髙虚以误人也。”如果有人想学静坐,应该以我的经历,稍稍有实效的东西告诉大家,不能自吹自擂,说得那么了不起,实际上以误后学。
无欲则静,虚而动直,然后圣可学而至矣。所谓自立门户者,非此类欤。佛氏教人曰静坐,吾亦曰静坐。曰“惺惺”吾亦曰“惺惺”。调息近于数息,定力有似禅定,所谓流于禅学者,非此类欤。仆在京师,适当应魁,养病之初,前此克恭,亦以病去。《陈白沙集》巻二)
“无欲则静”,没有欲望就静;“虚而动直”,如果没有执着、耽著,你的行为(动)反而会变得很正直;“然后圣可学而至矣”,到了这时候,你的圣学就可以学得很好。“所谓自立门户者,非此类欤。”如果自立门户就不是这样了。“佛氏教人曰静坐,吾亦曰静坐”,佛教说静坐,我也说静坐。曰“惺惺”吾亦曰“惺惺”,佛说惺惺我也说惺惺。(“惺惺”就是心的光明的意思。禅诗:“惺惺寂寂是,无记寂寂非,寂寂惺惺是,乱想惺惺非。”其中的“惺惺”就是不昏昧的意思。)
“调息近于数息,定力有似禅定,所谓流于禅学者,非此类欤。”调息就是数息,定力有似禅定。如果是有惺惺,这样去静坐的话,就不是流于禅学。儒家对禅很排斥,这里的意思否认自己流于禅学。“仆在京师,适当应魁,养病之初,前此克恭,亦以病去。”这是给他弟子写的信,说静坐可以养病,甚至能把病养好。说了一大堆,是说儒家静坐的一些要求,总的观念就是儒家的静坐方法跟佛家有类似之处,但他们的定达不到佛家这么深,见地也走不到般若那么深。
7)高攀龙
高攀龙是明代的大儒,是东林党的一个领袖,他非常的出名。名高攀龙,字存之,又字云从,南直隶无锡(今江苏无锡)人,世称“景逸先生”,“东林八君子”之一。听说魏忠贤要抓他,就跳水自尽了,后来崇祯又给他平反了。高攀龙留下了很多关于静坐的书籍,他特别喜欢静坐。
云:“静坐之法,不用一毫安排,只平平常,默默静坐。”(《高子遗书》卷三。)
静坐之法,什么都不用去安排,只需要坐在那里就行了,也不用排气、意守丹田。这个东西可以很高,也可以很低,大圆满也是这么修的,初学者也可以这样子。所以,静坐在那里做什么才重要。如果你说坐在那里啥都不做,那就最牛了。到底怎么回事,确实没那么简单。
《高子遗书》云:“学者静坐,是入门要诀。读书静坐,不可偏废。伊川先生曰‘节嗜欲,定心气’,静坐却是定心气之法。”、“朱子谓学者‘半日静坐、半日读书’,如此三年,无不进者。尝验之一两月便不同。学者不作此工夫,虚过一生,殊可惜!”
《高子遗书》是高攀龙留下来的唯一一本书,上面有很多说静坐的东西。儒家也要静坐、要读书、要闻思、要禅定、要戒慎恐惧,也有戒。“静坐却是定心气之法”,程颐说不要嗜欲,要让心气处于安定之间,静坐就是安定心气的方法。
“朱子谓学者‘半日静坐、半日读书’,如此三年,无不进者。尝验之一两月便不同“,这个内容,上面已经说过了,朱熹曾经告诉学儒的人,应该半日静坐、半日读书,坚持三年,没有人不会进步,即使坐一两个月,就会感觉不同。“学者不作此工夫,虚过一生,殊可惜!”学者不做此功夫,虚过一生。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静坐。
静坐是第一功夫。静中除妄想,是第一功夫。除得妄想,方是功夫。妄想如何除得?要知人生以来,眞心悉变成妄想。除却妄想,别无眞心。回光一照,妄想何在?妄不可得,即是真心急自认而已。日认日眞,必有日一声雷震,万户洞开,方知如上所言,字字是眞,字字是假。何者?不认不眞。当其认时,还是认者。故曰“是假”。当其眞时,即此认者,故曰“是眞”。此是儒者格物一诀,吾不知其于禅如何。(《高子遗书》卷十二)
“功夫”是指静坐的功夫,而不是武打的功夫。“妄想如何除得?要知人生以来,眞心悉变成妄想。除却妄想,别无眞心。”好像禅啊!他说人出生以来,真心全部变成妄想,要除去妄想,剩下的就只是真心——障垢磨尽,真如自现。但是不是呢?关键是真心除了以后,仅仅只是平静,或者仅仅处在中正仁义的状态里去治国平天下,那就不一定了。
“回光一照,妄想何在”,就像佛教的观心,念头在哪里,找不到念头。“妄不可得,即是真心急自认而已”,当发现妄想不在,妄不可得的时候,就是真心认识自己的时候(大圆满也是这么说的,稍稍一反观——真心自现,真有这么简单吗?)“日认日真,必有日一声雷震,万户洞开,方知如上所言,字字是真。字字是假。”天天这么去做,总有一天会一声雷震——普化一声雷,万户洞开,什么都明白了。到了这个时候,你就知道我上面说的字字是真、字字是假。
为什么呢?你不认,它就不是真。当其认时,还是认者,故曰“是假”。当你认到它的时候,认到的真心就是你能去认的那个东西,“假的”,就是你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意思。当其真时,即此认者,故曰“真”。你找的那个东西是找不到的——是假;你认的那个东西,“即此认者”——是真。“此是儒者格物一诀,吾不知其于禅如何”,这很像我们说大圆满。
“当其认时,还是认者,故曰‘是假’。当其真时,即此认者,故曰‘是真’”,反过头去看我们的真心,当其认的时候,会发现能认跟所认都是一个东西。所以,你认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——是假。“当其真者,即此认者”,不管怎么样,都只有一个认者,所以,这认者——是真。意思是什么呢?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被认的东西,认的东西本身就是它。这就是儒者格物的要诀,儒者的格物要格内心,“吾不知其于禅如何”,但是我不知道禅是怎么弄的?经常有人说陆王心学流于禅,所以他们经常去反驳,只要说禅,就认为不对。而我们说到禅,就觉得了不起,但那时候的宗派斗争就是这样的。
这是儒家的说法,照这么说,儒家的修行也很厉害,那儒家能不能证悟呢?不一定,儒家真的不能证悟,比道家还要差。但是,儒家要利益众生的,但利益众生的范围只是人,如范仲淹说: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儒家有利民、爱民的心;道家有出世的心。
达摩东渡前,他的师父告诉他“震旦有大乘的气象”,为什么呢?靠儒家和道家,形成民众有大乘气象。大乘佛教有两个特点,第一个是救度众生,第二个是寻得般若、证得般若。道家的禅定让民众有寻找般若的基础,儒家的利众之心奠定了民族可以实现大动机、大悲心,所以才有了震旦(中国)有大乘气象的说法。
儒、道奠定了我们民族的大乘气象,但儒、道本身不是般若。道家没有菩提心,只有禅定,见地不纯粹;儒家最麻烦的是没有出离心,也没有菩提心。你会发现,所有的标准都是用三主要道去套,为什么呢?因为三主要道的根本是般若道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般若说:世间所有的显现全都是虚幻的、虚假的,就奠定了出离心,一物都不能着。般若要求所有的众生都是佛,不能偏在任何一个有情上,这叫菩提心。般若不会是离开任何世间的一个东西,它就是这些东西,就是所有的有情,这是真正的般若(空性)——“空即是色,色即是空”,奠定了空性正见。一切都是来自般若的,所以学佛家的哲学,一定要学中观、唯识,把般若弄到尽处,就知道谁是谁非了。
为什么说儒家没有出离心呢?儒家学来是为了治国齐家平天下,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为了大家证得般若吗?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,儒家只是说立功、立德、立言,根本没有成佛、成仙的想法。
儒家不能证悟般若的根本原因
第一,无出离心,修行的基本动机是入世,导致不能放弃世俗,故而难以证悟般若;第二,无菩提心,虽然其宗旨是有利于人类,但却狭隘和纷乱,没有佛家菩提心的全面和深髓。为什么不全面呢?如对动物都没有全面的慈悲,指要求利益人,对杀动物没有太多的说法。利益人类社会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宗旨,最后基本上偏去忠君爱国,导致儒家偏向于统治集团;第三,没有皈依,不缘佛果,所以不能获得加持,没有清晰的般若见解,故不能在修行中融于般若。融入的就是一个平静,或者一个中正仁和(中正仁和到底是什么?其实是没有标准的,这就是关键)。
儒家不能证悟般若的见地原因
在见地上没有全面的般若见,不知全体即般若,由于不知全体即般若,就不知生命的来处和去处,从而不了解生命的根本,轮回的观念非常淡薄。儒家甚至都不提及六道轮回,孔子说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、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禅定多用于养气和静心。为什么要养气静心呢?动机耽于齐家治国平天下,即使是王阳明的心学,其境界也流于意识、禅定和功业运用层面,无法契入真实的般若境界。
儒家不能证悟般若的具体原因
道家追求成仙,认为成仙即脱离轮回,但儒家连这个都不提,导致在修行上没有具体的修行系统,虽然有静心养气、对境炼心、忠君爱民等各种思想和操行,但人和人之间、派别和派别之间,基本上各行其是,目标不清晰,过程不规范,没有清晰的次第和准确的结果。所谓的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,最多只是对一期生命成就的归纳,却丝毫不能说清楚生命真实的意义,固有:“儒家淡薄,收拾不住,尽归释氏”之说。
儒家追求立功、立言、立德,说白了,无非是功名利禄,非常的在乎。每个人都想权倾天下、富甲一方、名扬四海、艳与天齐。权倾天下,大家都很理解,要当很大的官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富甲一方,儒家也不拒绝财富,当然,有“君子固穷,不堕青云之志”之说,也有孟子“鱼,我所欲也;熊掌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,亦我所欲也;义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有甚于生者,故不为苟得也”之说。名扬四海,每个学儒之人所追求的人生。艳与天齐,是现代人的说法,所以,没有出离心根本就不行。
为什么说到艳与天齐呢?昨天讲到出离心的内容,在准备其上课的内容时,我突然想到了两位很著名的艺人——张国荣和梅艳芳,他们合唱了一首歌,叫《芳华绝代》,歌词是“唯独是天姿国色,不可一世,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。颠倒众生,吹灰不费,收你做我的迷。唯独是天姿国色,不可一世,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。颠倒众生,吹灰不费,得我艳与天齐……”
为什么我专门把这个拿出来说呢?大家可能有权倾天下、富甲天下、名扬四海的想法,但不会为之而沉醉,现代人沉醉什么呢?沉醉演艺、沉醉艺术、沉醉漂亮,艳与天齐。博客一打开、电脑一打开,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,明星怎么穿搭、怎么街拍,持靓行凶,只要一靓犯罪都不怕,长得漂亮、穿得漂亮作为是非的标准,这些想法挺可怕的。
《芳华绝代》前面还有一大段:“皇朝外的伊莉莎白, 谁来跪拜她 。梦露如果庄重高雅,何来绝世佳话。 红颜祸水锦上添花,教你荡产倾家。唯独是天姿国色,不可一世。”意思是有权、有钱都不咋地,唯独天资国色才能不可一世,这种天生我高贵还艳丽到底,要颠倒众生、吹灰不费,还要收你做我的迷。我们经常被别人收为做迷,老是看别人穿搭穿搭——穿搭什么啊?不穿最好了!孙悟空说“齐天大圣,命与天齐”,这首歌还来“颠倒众生吹灰不费,艳与天齐”,好牛哦!
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国荣和梅艳芳,后来陈奕迅等歌手相继翻唱,当时真的唱得不可一世啊,结果呢?虽然张国荣是不一样的烟火,但烟火还是要熄的,而且熄的方式极其惨烈,跳楼自杀了;梅艳芳最后癌症去世,临终前还举办了一个演唱会,最后献上的歌是《夕阳之歌》,歌词“奔波中心灰意淡,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,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……”,想归去已经不行了!
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?艳与天齐,最后就是归去但已晚,不要沉醉于此。我们这个时代,可能不会沉醉于权倾一方、富甲十方、名扬四海,但你偏偏被那些明星收成了迷,整天研究别人的穿搭,没有出离心,想归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。
现代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?
“白天要工作挣钱,晚上要上网游玩,爆米花填满电影院,运动大都在百货店。为了支付宝纠结,在抖音上摇晃,微博上装模做样,实际上孤独惆怅。朋友圈人模狗样,私下里黯然神伤,整天作诗和远方的想象,现实中只有苟且憔悴和失望。”
我也写了一首诗来描述,现代人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?你们为什么不学佛呢?
红楼梦的《好了歌》: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;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。世人都晓神仙好,惟有功名忘不了!古今将相在何方?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金银忘不了!终朝只恨聚无多,及到多时眼闭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娇妻忘不了!君生日日说恩情,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儿孙忘不了!痴心父母古来多,孝顺儿孙谁见了?”
“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金银忘不了!终朝只恨聚无多,及到多时眼闭了。”这个时代最喜欢钱了。“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娇妻忘不了!君生日日说恩情,君死又随人去了。”这还是古代,要君死才随人去了,现在是你还没死,也随人去了。“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儿孙忘不了!痴心父母古来多,孝顺儿孙谁见了?”我们民族天生对世法采取失望的态度,读了这些东西,不是避世,而要去修行学佛。
避世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讲的: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是非成败,没什么了不起,秋月春风穿搭得非常好,也没什么了不起,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,一笑了之,淡淡的活着是最好的,平常的生活是最好的——狗屁,不是这样的,你一定要去修行,否则没法在笑谈中,因为有生死、有轮回,这些见解是不透的。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没有出离心、菩提心,否则是不行的,你的生命会浪费。
如前所说,佛家为什么老是用三主要道去评价儒、道两家无法证得般若?因为菩提心是根据般若见来的。
评价理由:
认知本性,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障碍认知准确的人我执着。什么意思呢?若想发现般若,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消灭我执,因为人我执障碍我们认知本性,故需菩提心,还需空性正见。空性证见是理性的意识的目标,而去体认的时候是非意识的,非意识的人我执会障碍非意识的认知,所以要消弱人我执,才能够准确的认知。若想消弱人我执,就一定要修菩提心,这是其一。
其二,若想真正的达到般若,一定需要已经达到般若之境的三宝和般若本身的加持。什么叫般若本身的加持呢?比如把《金刚经》往头上一拍,那就是加持;去恭敬它、去阅读它,都可以得到加持;在修行中,遇到各种顺缘,境界能够迅速现前,这是三宝的加持。三宝就是般若的直接投射,没有这些加持真的不行,因为最终要融入三宝、融入般若的本质,它们本来一体,不去皈依它的话,就无法证悟。由于儒、道两家没有般若之说,没有皈依就得不到皈依的加持,也没有菩提心的强烈认知,不免偏颇,最终无法证得菩提。
此评断标准似乎立足于佛家学说,但从哲学意义上讲,佛家般若见确实是对事物的最根本究竟的认识,中观里面的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,说任何现象的本质是本弱,而般若并非离开现象的独立事物。它不是什么无极,也不是恍兮惚兮的其中,也不是中正仁义的心态,它就是一切。
由于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,若想认知本质,就要离开现象,就是出离心。由于般若见认为所有有情全是平等,所以必须要有菩提心,这样才能融入“全体即是般若,般若即是全体”的般若见。这是哲学观点决定了儒和道无法证悟般若,因为没有缘一切众生的菩提心,也没有缘佛果的皈依心。这不是张嘴乱说,而是有逻辑性、哲学性的,若要确定般若是究竟见,就是中观所讲的内容。所以,无菩提心无法证悟般若,没有加持无法证悟般若。
至于必须获得加持才能证悟,是因为般若见并非佛陀创造,只是经由他教导。就算佛陀没出现,般若见也是世界的真理,而且般若见也不是佛陀才开始的,无始的佛陀早就出现了,并没有佛教一步步发展起来之说。
佛教的道理标准并非是由人类分别念堆积、发展起来而形成的,实际上就是真理,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,引导我们去寻找它。在寻找的过程中,现成的真理就是他要对我们进行加持,我们也必须有信心去皈依和加持,否则无办跟他们融为一体。
所以,用菩提心去衡量儒、道两家不能证悟的标准,是因为般若见,而般若见是可以通过逻辑进行追寻、学习、探究。讲来讲去,佛、道两家,还是佛家最厉害,因为我们学中观、学唯识,中观的一部分是格物,比如通过离一多因来格外面的东西,唯识就是格内心,修行就是具体的格。
印度哲学:六师外道、印度教
数论派:数论派有两个词汇:一个是自性,一个是神我。认为自性是一切事物转变的根本因(任何一个现象的根本点叫自性),却不是唯一的因,认为存在一个与自性并列的独立的精神实体——“神我”。
六世外道里面,数论派是最高的,他认为万事万物有两个根本,一个是事物的“自性”,一个是使之产生变化的“神我”,神我自身不演变出世间事物,却可以与自性结合,从而使自性开始演化。实际上,“神我”就是人我执,“自性”就是法我执。
印度教:人格化的三个神祇:大梵天、湿婆、毗湿奴——大梵天是创造的,湿婆搞破坏的,毗湿奴是保持平衡的,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成住坏空,但是,造成这个世界成住坏空的一个本体称为“梵”。
商羯罗是印度中世纪最大的经院哲学家,公元640~690年。他创立了不二论,即一元论学说,认为除宇宙精神梵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物,梵和个人精神是同一的、“不二”的。为人们指出了如何摆脱虚妄,达到真实的道路。在他看来,物质、个人灵魂、具有人性的神又都是存在的,但从总的真理的意义上来说,这一切都是幻觉,是梵以幻力进行了神秘而不可喻解的作用的结果。
这一大段的是说根本是“梵”,梵可以产生神、产生个人的灵魂、产生一切——一元论,“梵”是最根本的,其他都是假的,所以是不二。
他认为,把幻象当成真有,是以人自身的无知无明为条件的,并强调指出:“只有智者可以透过它看到它背后除了唯一实在的梵之外别无他物。”普通人会把幻象看成真实,智者可以看到事物背后的唯一实在,就是梵。
但“梵”和“空性”却不是一个东西,听起来好像是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,其实不然,意思是一切东西是梵,但梵不是一切东西——梵可以组成一些东西,但梵不是一切东西,因为没能走到底,有点像微尘组成世界,但世界不是微尘;世界是无极,但无极不是世界;而佛教就是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。
这里列出了梵与空性的五个差别体现,时间问题,你们可以自己去看。总之,印度哲学也一样无法走到全体般若的般若程度去,只有佛家说“一切现象都是空性,而空性没办法离开一切现象”。
大家问:“那法性定是什么呢?”法性定是一种定,只是让我们体认了空性而已,虽然它是应成派的见地,但并不是说法性定是一个单独与现象分割开的东西。从哲学上可以说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,从修证上、境界上去说,证实色即是空的“空”是处于法性定中间,这是修行境界上的一个状态。
从哲学上、从我们的认知上,可以说一切都是空性,那为什么我们见到色,而不见空呢?因为我们不知道“空”是什么,没有经过法性定,就像我们见到张三而没有见到李四。对我们来说,“空”只是一个概念,没有真正的认知。如果认知了,就会发现,处于色的状态里面就是空——处于有色的普通状态(色),如果真的见过空的话,就会认为这些色就是空,没有真正的色。空会表现为这些色,色也是空的一种表现而已,没有一个色相是真实的,随起随灭,根本不存在。勉强可以当作一种般若幻象、法性游舞,但没有一个有相的色是真实存在的,而这个空根本就没有真实不真实的说法。
所以,“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”在哲学上很难理解,同时也很难实现。如果实现了,再去看梵、无极就觉得很简单,儒家就更简单了(儒家无非是把心态搞得好一点,用去建功立业的方法。当然,儒家里面有利众的想法,但只是利人类,由于没有般若见,就只要利益社会、忠君爱国,绝对不会说爱一切众生。儒家里面没有说杀动物不妥,因为从不把动物看成佛陀。所以,没有正确的般若见,就没办法证悟般若。)
总之,根本的哲学见地一定要落到佛家的哲学、佛家的认知上,这才是学佛人最根本、最究竟的哲学见地。还有一个特点,佛家的哲学见地是可以实现的,不仅仅是思维或者走不到极处,如道家也有修行,但走不到极处。
好,今天的交流到此结束,现在开始回向。
【注:文稿内容未经讲授者本人审核校对】